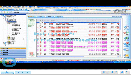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普世價值觀。以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為主題的低碳經濟,作為全新的市場規則和運營環境,對傳統物流企業的發展和轉型升級提出了“綠化”的要求和挑戰。也許目前的“綠色”環境與我們的期待還有很大差距,但這并不能成為物流企業放棄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之社會責任的理由。畢竟低碳經濟還處于發展初期,我國綠色物流發展還剛剛起步。物流企業需要在“綠化”的過程中完成低碳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定位。
一、遏制氣候變暖的目標
全球極端氣候現象已經成為新常態(New Normal)。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的排放,以有效遏制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發達國家的研究預警表明,如果全球氣候變暖超過2℃這個底線,將導致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海洋、海岸帶生態系統崩潰;一些沿海低地國家及島國被淹沒;熱帶地區將因氣溫升高而導致糧食大量減產,極端天氣頻發,生物生存環境改變,缺水人口將達20億。因此,應在本世紀將氣溫升幅控制在2℃之內,這是人類社會可以容忍的地球升溫的最高限度。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以下簡稱IPCC)2007年的報告指出,為實現本世紀將地球升溫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發達國家應承諾到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5%—40%。但實際上,發達國家僅承諾減排12%—19%。
據測算,2020年以前,全球共需減排140億噸,而有承諾的減排量只有90億噸,其中發達國家承諾減排37億噸,發展中國家承諾減排53億噸,全球碳排放減量缺口達50億噸。因此,IPCC預計,2020年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將超過2.5℃,甚至達到5℃,超過2℃導致災難性氣候變化的概率達50%。且保守估計,到本世紀末,全球海平面還要以平均每年4毫米的速率繼續上升,到2050年,全球將有大約2億人被迫離開家園,成為“氣候難民”。
盡管國際社會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上就對“2℃目標”達成了基本共識,并在2010年墨西哥坎昆氣候變化大會上設定了2℃的控溫目標,但在減排責任承諾上,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歧過大,遲遲不能就2012年以后第二階段的減排承諾與相關協調機制達成一致,而且39個發達國家和轉型國家第一階段減排承諾能否真正兌現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2007年以后,全球碳排放增長已經遠遠超出了預期。
二、全球碳排放超量增長
雖然IPCC的預警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但在以發展本國經濟為首要任務的情況下,全球碳排放繼續超量增長。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研究,201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達306億噸,比上年增加16億噸,比2008年創下的歷史紀錄增長了5%,其中3/4來自新興經濟體。而要實現2020年之前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這個數字不應超過320億噸。如此看來,未來10年,除非各國采取果斷措施,否則把碳排放增量控制在14億噸之內幾乎是不可能的。
美國能源情報署(EIA)2011年的一份報告預測,受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強勁需求的拉動,未來25年內煤炭的使用量將繼續增長53%,化石燃料將繼續占世界能源的80%。到2035年,全球市場的能源消費量預計增長53%。如果沒有重大的政策改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從2007年的300億噸增加到2035年的420億噸,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多。另據IPCC預測,如果碳排放仍然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100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超過4℃的可能性達50%。
遏制碳排放成本驚人。根據麥肯錫公司的測算,要將地球升溫幅度控制在2℃以內,最樂觀的情形是,到2030年全球每年減排成本為2000億—3500億歐元。在油價為每桶60美元的情況下,到2020年每年需要的增量投資約為5300億歐元,到2030年達到每年8100億歐元。如今,國際油價已經上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必然導致相關減排成本極大上升。
三、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國
1.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劇增
我國經濟已經持續多年高速增長,但能源消耗強度大,能效不高,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劇增。根據世界銀行2009年報告,2007年我國(大陸)向大氣排放了65.33億噸二氧化碳(比2006年多4.25億噸,比2005年多9.24億噸),超過美國同期排放量7億多噸,首次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306.49億噸的21.3%;人均排放量為5噸,在已有數據的196個經濟體中排名第73位。
此后的發展勢不可擋。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P)的研究報告,2010年,我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能耗增長11.2%,全年二氧化碳總排放量83.3億噸,增長10.4%,占全球排放總量的25.1%,而同期全球總排放量僅增長5.8%。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能源結構仍然以煤炭為主。2010年,我國煤炭使用量增長了10.1%,消耗了世界上48.2%的煤炭,全球煤炭生產上升了6.3%,而我國增加了9%,估計拉動內需的4萬億元投資對此貢獻不小。
從碳排放結構看,我國火電排放占41%,增長最快并持續增長的汽車尾氣排放占25%,其余是建筑排放,占27%。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制的《中國城市低碳發展2011》綠皮書特別指出,30年內,若沒有顯著的技術變革與結構轉型作支撐,加之人口增長、人均GDP增長與居民生活質量提升,我國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總量會一直處于增長狀態。報告估計,2035—2045年間,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將達到頂峰,徘徊在130億噸左右;到2045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將接近9噸。
2.能耗強度居高不下
2010年,我國GDP超過40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4%;全年能源消費總量為32.5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5.9%,比2005年增長37.7%。得益于政府各項節能減排措施的有效實施,我國萬元產值能源消費量下降了4%,但能源消耗強度仍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歐盟的3.8倍。雖然我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但日本能源消費總量僅為6.6億噸標準煤。
從運輸業能耗水平看,我國載貨汽車油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30%左右,乘用車單位油耗水平比歐洲高22%,比日本高39%,內河運輸船舶油耗比國外先進水平高20%以上,機動車尾氣排放在一些大城市占大氣污染物的比重達60%。一般認為,我國交通運輸業占用了社會總能耗的9%左右(其中石油消耗約占34%,碳排放約占25%),僅次于制造業。
我國整體能源利用效率約為33%,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主要耗能產品的單位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要高出25%—60%。
3.發展與減排高度糾結
(1)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能源支撐。2010年,我國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僅為日本的1/10,排世界第94位;2011年,我國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折合2130美元,不及美國同期的1/7;2010年底,我國城市化率為47.5%,預計2015年將超過51%。
從人均能源消耗水平看,根據國家能源局的數據,2010年,我國人均能源消費量為2.43噸標準煤,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僅為美國的23.6%,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家的38.7%;人均用電量3200千瓦時,人均油耗O.29噸,分別是美國的1/4和1/10。即使按照德P世界能源統計2011》的數據,2010年我國人均能源消費量為1.77噸油當量,也才略高于世界人均水平1.74噸油當量。
從發展來看,我國能源總量供應不足問題將長期存在。據《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11)》預測,“十二五”期間,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將增加8億~10億噸標準煤,年均增長4.8%~5.5%,到2015年能源消費總量達41億~42.5億噸標準煤。
為此,國際能源署(IEA)首席經濟學家比羅爾(Fatih Birol)2010年提出,未來20年內,我國需要在能源領域投資約4萬億美元,以便為經濟提供動力,避免發生停電和燃料短缺;未來15年,我國將新建約10億千瓦裝機容量,基本相當于美國現在的總發電量,而美國是用數十年才建立起來的。
(2)節能減排壓力巨大。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確定的節能減排目標為:到2015年,我國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據此,我國在“十二五”期間要實現節能6.7億噸標準煤。但實際情況卻是,加1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增加了1.5億噸,2011年增加了2.3億噸。如果這種上升勢頭不減,后期減排壓力將越來越大。
從目前的情況看,2012年我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已調低到7.5%,2012年一季度GDP增長已回落到8.1%,工業和重工業用電量增幅分別同比降低了7.6%和7.4%,京、滬、浙、粵等經濟發達地區1~2月份工業增加值增速同比幾乎下降了66.7%。預期全年能源消費增幅可能會放慢。
四、環境污染治理成本迅速增加
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于2006年9月7日聯合發布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公眾版)》。這是我國第一份經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研究報告,即綠色GDP報告。報告顯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如果按照當時的技術水平對2004年點源排放污染物進行全面治理,需一次性直接投資約10800億元,占當年GDP的6.8%左右。同時,每年還需另外花費治理運行成本2874億元(虛擬治理成本),占當年GDP的1.80%。而我國“十五”期間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僅占GDP的1.18%,環境欠賬之大不言而喻。
上述數字觸目驚心,可謂環境污染猛于虎也!但實際情況仍在繼續惡化。國家環保部環境規劃院2010年12月發布的我國第二份綠色GDP報告——《中國環境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8(公眾版)》披露,2008年我國生態環境退化成本達到12745.7億元,占當年GDP的3.9%;環境治理成本達到5043.1億元,占當年GDP的1.54%。特別令人矚目的是,與2004年相比,我國環境退化成本增長了74.8%,虛擬治理成本增長了75.4%。2008年,GDP環境污染扣減指數為1.5%。報告還顯示,2008年環境污染成本比2007年增加了1613.5億元,增長了22.0%,增幅略高于2007年,但遠高于同期9%的GDP增速。
麥肯錫公司認為,未來中國每年要將1%的GDP用于減排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按2011年47.2萬億元GDP計算,應該是4715億元。實際上,《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確定了“十二五”全社會環保投資需求約為3.4萬億元。
但據世界自然資源研究所(WRI)分析,從節能技術應用來看,還有眾多節能減排技術我國并不掌握,基準減排情景下需要的六十多種技術,有四十多種核心技術不在我們手里。這就意味著,我國為履行對國際社會的減排承諾,可能還要花費大量投資從發達國家引進相關節能減排技術。
錢從哪里來成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麥肯錫公司的建議是,可通過控制出口配額多寡,換取發達國家的減排技術。即使這個可以暫且不論,在享受了“黃金十年”的高速發展紅利以后,現在恐怕也要反過來投資治理環境污染了。
問題是,我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還可持續嗎?物流業現有的運營模式還可持續嗎?
五、物流業節能減排路徑清晰
作為全球三大二氧化碳排放源之一,物流和運輸業節能減排潛力巨大。根據埃森哲咨詢公司2009年《世界經濟論壇——供應鏈低碳化報告》,全球運輸業每年排放溫室氣體約28億噸。占人類活動溫室氣體排放量的5.5%左右;公路貨運碳排放超過15億噸,約占物流和運輸部門總排放的60%:物流和運輸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占產品生命周期排放量的5%~15%,其中運輸排放占80%以上,倉儲建筑物排放約占17%;能源成本約占交通運輸企業生產總成本的30%~40%,但有6%的燃油被消耗于交通擁堵。如物流業進行環保改革,每年可為全球減少14億噸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約占所有人類活動排放量的近3%。
另外,根據國際海事組織(IMO)的報告,航運業承擔了全球80%的貿易運輸量,年碳排放量超過10億噸,僅次于公路運輸碳排放量,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3%~4%,且有迅猛增長之勢。好在國際海事組織(IMO)已于2011年7月頒布了旨在提高船舶能效性的兩項強制標準。
顯然,“綠色”公路運輸和“綠色”海洋運輸將成為物流業節能減排的重中之重,也是綠色物流發展的機會所在。幸運的是,我國2011年交通運輸業節能減排取得明顯成效。據交通部《2011年交通運輸業節能減排工作總結》披露,與2005年相比,2011年我國營運車輛單位運輸周轉量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下降10%和11%。營運船舶單位運輸周轉量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下降15%和16%。與2010年相比,民航運輸噸公里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均下降3%以上。交通部樂觀預計,通過提高能效水平實現節能減掃“十二五”目標的空間很大。
盡管目前還沒有權威的有關物流設施碳排放強度的具體報告,但考慮占產品生命周期碳排放量17%的倉儲建筑物排放,我國上千萬平方米數量級倉庫或配送中心的節能減排、上億平方米數量級物流園區的節能減排潛力也非常值得期待。
六、物流企業“綠化”之路
在了解上述綠色物流發展所處低碳經濟環境狀況后,傳統物流企業“綠化”路徑也基本確定了。
1.加強節能減排管理
埃森哲咨詢公司在2009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供應鏈低碳化報告》中指出,物流與供應鏈管理活動中最具潛力的減排措施有五個:一是采用清潔能源交通工具,約可減排1.75億噸二氧化碳;二是按照效率原則優化配置農業和工業生產地點,可減排1.5億—3.2億噸;三是適當降低運輸速度并增加一次載運量,可減排1.71億噸;四是減少產品外包裝體積和重量,可減排1.32億噸;五是改進物流系統布局結構,可減排1.24億噸。
對此我們不用懷疑,因為上述五個有潛力的綠色物流活動,傳統物流企業一直在做或孜孜追求,只不過在企業發展戰略中還缺乏明確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和戰略表述,還沒有按照標準規范對物流活動碳足跡進行核算,并據此制定明確的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目標以及調整企業運營模式罷了。因此,綠色物流并非一個全新的概念,而是一個更為全面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節能減排就在日常運營之中。
2.做好低碳運營適應性調整
與企業過去主要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戰略定位不一樣,低碳經濟要求企業根據環境可持續發展要求——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硬約束——做企業運營適應性調整。適應什么呢?適應國際和國內低碳經濟法規要求,適應產業技術和管理標準規范要求,適應供應鏈系統節能減排要求,適應企業自身發展戰略和運營特點要求。
物流企業適應低碳經濟運營環境的過程就是所謂“綠化”的過程。為此,傳統物流企業要關注低碳發展和全球環境變化,關注政府相關法律和產業政策的變化;要努力提升制定低碳物流和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的能力,創新低碳客戶服務模式;要在傳統決策模式基礎上,依法把物流活動造成的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降級成本等外部成本內部化,一并納入企業物流管理活動的成本效益考量,并據此調整企業綠色發展戰略和經營模式。簡單來說,物流企業綠色核算就是要在現有物流服務收益中,按照公認的標準和方法對資源耗減成本與環境降級成本來作必要的扣除。可用公式表示為:
綠色物流=物流業增加值-(物流資源耗減成本+物流環境降級成本)
與之相應,綠色物流總成本計算公式調整為:
綠色物流總成本=運輸成本+倉儲成本+存貨占用資金成本+一般管理成本+資源耗減成本+環境保護支出+環境污染損失和治理成本
由此可見,在現有物流業增加值不變的情況下,依法需要扣減的外部成本越小,說明物流企業“綠化”越成熟。
3.盡快開展碳足跡認證
由于企業綠色物流總成本計算口徑增大,且需要超越傳統企業邊界計算外部成本,專業性特別強,因此需要借助專業第三方認證機構力量。作為通向綠色物流的技術和管理路徑,也作為接入全球供應鏈體系實現國際化運營的通行證,物流企業應像對待ISO9001:2008質量管理體系認證那樣,積極創造條件,按照國際公認權威標準——英國QAS 2050:2008商品和服務在生命周期內的溫室氣體排放評價規范》和ISO14000環境管理系列標準》——進行企業碳足跡認證,并支持客戶實施碳標簽制度。
4.積極融入客戶供應鏈節能減排體系
必須指出,“物流管理是供應鏈管理的一部分”,并不因物流“變綠’而改變。從供應鏈管理的觀點來看,正如物流業的服務要通過客戶競爭力的提高來體現其市場價值一樣,物流業減排也需要供應鏈合作伙伴的協同,其市場價值最終將體現在客戶企業產品與服務的碳足跡認證和碳標簽上。正因為如此,埃森哲咨詢公司認為,物流業“60%的減排潛力來自物流業本身,而40%的減排潛力將通過整合更廣泛的產業來實現”。
因此,物流企業要積極融入客戶供應鏈的節能減排體系,在為客戶制定解決方案的同時,與客戶一起制定物流節能減排方案,并將之作為總體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物流企業要逐步培養影響上游供應商與下游客戶自勺“綠色”影響力,即提升綠色供應鏈資源整合能力。這不僅對物流企業提出了減排專業技術和服務能力的要求,而且提出了更高的可持續發展的道德要求。
5.積極實施“綠化”戰略投資
毋庸諱言,發展綠色物流在短期內將增大物流企業運營成本,可能會使其收益變成以正外部效應(負責任的企業形象、客戶忠誠度的提高、鞏同供應鏈伙伴關系等)為標志的長期品牌收益,而“綠化”項目的資本支出和機會成本,則有可能成為企業短期甚至長期的經營負擔。此外,企業外部負效應成本核算如果沒有國家強制性法規約束,也很難實施。因此,發展綠色物流需要在國家層面上建立綠色物流發展機制,來推動、資助、協調企業“綠化”戰略投資,把可持續發展理念真正變成企業自覺的有利可圖的經營行為。
總之,物流業發展面臨嚴峻的“綠色”挑戰,包括國際環境壓力、政府規章要求、行業組織規范、企業競爭需要以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總體、系統的綠色供應鏈管理或將在不久的將來取代局部、環節的綠色物流管理。
核心關注:拓步ERP系統平臺是覆蓋了眾多的業務領域、行業應用,蘊涵了豐富的ERP管理思想,集成了ERP軟件業務管理理念,功能涉及供應鏈、成本、制造、CRM、HR等眾多業務領域的管理,全面涵蓋了企業關注ERP管理系統的核心領域,是眾多中小企業信息化建設首選的ERP管理軟件信賴品牌。
轉載請注明出處:拓步ERP資訊網http://m.hanmeixuan.com/
本文標題:低碳經濟環境與物流企業“綠化”
本文網址:http://m.hanmeixuan.com/html/consultation/10839380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