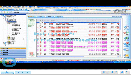經濟發展導致了企業管理的兩權分離,而兩權分離則帶來了經理人與股東利益目標的不一致,從而產生了經理人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股東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和“道德風險”。因此研究經理人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成為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熱門話題。很多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特別是詹森和邁克林(Jense&Meckling,1976)的代理成本理論提出以后,經過不斷的完善和發展,已經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前提和委托一代理理論的框架下,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體系,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由于“理性經濟人”假設本身的某些局限性,使得經濟學對于在現實中存在的很多現象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讓人們感到十分困惑。產權經濟學家所強調的所有權激勵與經濟行為之間內在聯系使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產權明晰化是減少交易成本、克服組織內部投機行為的有效途徑。但正如德姆塞茨(Densetz,1988)所說,在許多情形下,一個企業的產權是“殘缺”的。人們忽視了控制權產生的巨大能量,現實生活中,控制權爭奪遠遠超出對剩余索取權的追求。比如,我們經常聽到經理們抱怨有效激勵不足的呼聲,卻很少看到經理主動辭職的現實行為,他們利用手中的控制權獲得在政治仕途、聲譽、資源轉移等方面的額外收益,還有過度的在職消費、明目張膽的高薪自定等情形都是屬于企業產權弱化的現象。目前的解釋只能說這是缺乏效率或者說是無效的,特別是對我國不同所有制企業經理人薪酬的差異更不能給出進一步讓人信服的理由。因此,我們試圖在威廉姆森關系合同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合同治理結構和嵌入人際關系的分析來對企業經理人的報酬契約進行新的詮釋。
一、經理人報酬契約的本質:關系合同
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而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企業經營管理者進行激勵約束的經理人報酬契約是這一系列契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人力資本獨特的產權特征也決定了報酬契約有著不同于其他契約的屬性。首先,與除人力資本以外的任何經濟資源可以屬于任何的個人或集體不同,人力資本的“所有權限于體現它的人”,即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離性,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所有權;其次,人力資本天然屬于擁有它的個人的特性,使得當人力資本產權束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刪除時(即出現德姆塞茨意義上的產權殘缺時),產權的主體可以將相應的人力資產“關閉”起來,從而使這種資產的經濟利用價值頓時一落千丈(周其仁,1996);再次,人本資本具有資產專用性的特征。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縱向一體化能有效解決因“資產專用性”而導致的“敲竹杠”問題,但含專用性人力資本的縱向一體化卻不能解決敲竹杠問題(張立君,2000)。為實現作為人力資本所有者的經理人和非人力資本所有者的股東之間的“和平共處”,他們之間所簽訂的契約也必然是與資產高度專用性和頻繁交易密切相關的“關系合同”,而不應是古典合同或新古典合同。
具體而言,經理人與股東之間需要維持一種長期的穩定關系才能有助于企業的正常發展。對于報酬契約的簽訂,雙方之間的具體身份非常重要,而經理人的人力資本的投入也不是一次性的,它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因此從資產專用性的意義上說,經理人通過報酬契約投入企業的人力資本是一種高度專用性的資產,高度專用性的資產就意味著資產一旦投入,股東想要更換它的機會成本就會很大,對機會主義造成的傷害也很大。因此對于這樣一種具有高度專用性的資產,股東需要保持與經理人關系的持久性來換取未來收益的長期穩定,而不是通過市場的有效性來治理。所以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報酬契約更加適合用關系合同來治理。
二、關系合同的嵌入性結構分析
威廉姆森的關系合同理論認為,將具有特定身份的人際關系嵌入到雙方簽訂的合同當中,可以減少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交易成本并維持合同雙方交易的持續性。但這一理論建立在如下假設之上:成文合同所體現的治理結構(以下簡稱“合同治理結構”)和嵌人其中的人際關系之間沒有摩擦。但基于如下原因,這一假設實際上是不成立的:首先,關系合同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人際關系存量作為依托,這種“約前人際關系”既可能促進關系合同的形成和有效履行,也可能因與成文合同所體現的治理結構不相適應而成為關系合同履行的障礙;其次,“人際關系”是一個具有多元屬性的關系叢,不同的屬性不可能得到清晰的分離,因此,在將人際關系嵌入合同治理結構時,就不可能有選擇性地將有利于合同治理結構的人際關系納入其中,而將不利于合同治理結構的人際關系排除(劉世定,1999)。因此,現實當中,關系合同的兩個維度——合同治理結構與嵌入其中的人際關系——之間的摩擦無可避免。
為深入分析合同治理結構與嵌入其中的人際關系之間的關系,劉世定(1999)將合同治理結構進一步分為權威治理和雙邊治理兩種形式、將嵌入人際關系進一步分為影響力對稱結構和影響力不對稱結構,四種情況組合就形成合同治理結構和嵌入人際關系的四種基本對應關系。在這四種基本對應關系中,如果合同治理結構與嵌入人際關系的影響方向相同時,這種對應關系就被稱之為“同構”,否則就被稱之為“非同構”。在“同構”的對應關系中,嵌入合同治理結構中的人際關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合同不完全所產生的交易費用,或者合同治理結構與人際關系之間的摩擦所產生的交易費用小于人際關系對合同不完全所產生的收益。相反,在“非同構”的對應關系中,合同治理結構與人際關系之間的摩擦可能導致關系合同無法履行。
三、對經理人報酬契約的嵌入性結構分析
從前文對關系合同的交易特征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對于企業經理人報酬契約的合同治理。由于人力資本的高度專用性和需要維持雙方關系的長期穩定,它更適用于關系合同。而合同治理結構與嵌入其中的人際關系之間的摩擦可能導致關系合同運行中出現合同約束軟化現象。為了維持長期關系,常常要在合同實施的嚴格性上做出讓步。合同約束軟化意味著對與合同相聯系的預期利益的調整,它既會導致生產成本提高,也會有交易成本存在。對企業的經理人報酬契約來說,它的簽訂過程就是股東與經理在企業產權的邊界劃分上的不斷模糊、轉讓和討價還價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股東的部分產權會向經理人發生模糊、轉移。站在經濟學的角度上看,這是種產權不清晰的表現,會產生交易成本和企業內部的投機行為,是會損失企業的“效率”的。但這是在經濟學的“經濟人”不需要聯系的匿名活動前提下出現的效率損失現象。這就像是博弈論中的經典模型“囚徒困境”,在雙方缺乏溝通和匿名行動的情況下,雙方都會采取最有利于自己卻造成了共同收益最小化的方案。而在雙方知道可以得到充分溝通以及需要維持長期聯系的情況下,雙方合謀采取共同收益最大化方案的動態合作博弈是可能發生的。因此站在關系產權的角度上看,產權是一束關系,企業以犧牲部分暫時的產權來換取一種長期的穩定合作(周雪光,2005)。這能很好的解釋企業內普遍存在的經理人在職消費行為,這就是股東對于經理人的一種產權轉移,用科斯(COAse,1960)的社會成本觀點來看,這就是一種增加交易成本,影響企業價值的交易費用。但在關系產權理論看來,這恰是股東通過自身產權的部分模糊和轉讓來達到對經理人的一種“隱形激勵”,從而促使經理人為企業的長期發展考慮,是維持雙方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所必須做出的犧牲。這也是關系合同治理中的合同軟約束的一種表現,但他們的共同目標其實都是用一種短期交易成本的增加來換取長期的穩定收益。
前文分析表明,在非同構條件的經理人報酬契約中,通過關系來彌補合同的不完全時,會出現結構性摩擦。一方面,結構性摩擦會影響關系合同治理的基礎,股東通過關系合同來治理經理人的報酬契約的實質就是要用企業產權的模糊和部分轉移來充當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目標利益函數沖突的潤滑劑,緩解雙方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對經理人的長期“隱性激勵”,使股東的遠期利益最大化。而非同構的條件下合同治理結構與嵌入人際關系之間的摩擦會影響到充當潤滑劑的“關系”本身,在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產生一種關系上的摩擦,進而影響到關系合同治理的效果。因此非同構的組合對于經理人報酬契約的關系合同治理而言不但沒有起到對經理人的長期“隱性激勵”作用,反而還增加了企業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從關系產權理論的角度看,一定的制度邏輯界定了一個組織的交往方式或內部運行的方式。而非同構的合同治理結構和嵌入結構的組合則會破壞由一定關系產權決定的制度邏輯,這種結構性的破壞會扭曲企業的行為特別是經理人的行為,從而徒增企業的代理成本,因此當合同治理結構嵌入了不同質的關系結構,雙方小心地調整關系邊界和合同治理結構的硬度成為關系維持的必要條件,調整不當則會導致關系破裂。
以上筆者分析了關系合同理論對于企業經理人報酬契約的治理機制,但是并沒有考慮不同產權結構引起的嵌入結構的差異。對于關系產權來說,一定的關系產權決定了相應的制度邏輯,而這些制度邏輯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一個組織的交往方式或內部運行的方式,從而限制了企業的相應行為(周雪光,2005)。而在我國,特別是在進入轉型經濟的今天,國企與私企有著截然不同的產權結構,經理人的報酬契約的形式和嵌入結構也有所不同。
對于國有企業而言,它是國家所有,是一種公有制經濟,除了做為一個普通的市場主體,它還肩負著國家的宏觀和微觀經濟調控任務,因此國家通過其特有的權力對于企業的干預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大型國企的內部合同治理結構屬于權威型的不對稱結構,這種權威型的不對稱結構會產生政府和經理人之間以及經理人和員工之間的結構性摩擦。如,經理人與員工間的報酬契約差異過大,會導致員工將經理人視為“外人”,破壞員工與經理人之間心理契約的聯系,造成員工與經理人對立,產生結構性摩擦,影響組織公平,降低企業效率。而在公有制體制下,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國企作為經濟發展主力軍的同時也肩負維持社會公平的責任。但經理人會因為個人價值沒有得到貨幣體現而產生強烈不滿,會利用控制權,如內部權利調整、盲目擴張、重復建設、抵制兼并重組等為自己謀求報酬以外的“灰色”收入。這種結構性摩擦會損害國有企業的利益,政府通過職務的升遷和在職消費等隱形激勵消除經理人的“不公平”心態,以增強經理人決策目標與企業長遠目標的一致性。因此,對于人力資本專用的經理人報酬契約雖然采取的也是講究產權模糊的關系合同治理,但是為了防止結構性摩擦產生進一步的交易成本,國企的嵌入結構更傾向于影響力不對稱的關系結構。國家傾向于通過保持國企經理與員工報酬契約的相對同步性來維持企業內部制度邏輯的穩定,因此,國企經理層的選用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一般通過行政任命,并且經理人的報酬方式更多的是一種類似國家公務人員的行政保障體制,形式相對比較單一,這都是由國企的內部權威治理結構決定的。而對于廣大的民營企業而言,它的所有權結構以私有經濟為主體,國家只能通過制定法律等同時影響所有企業的方式來間接的規范企業的行為,它不會直接干預企業的行為,所以民營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屬于平等型的對稱結構。在政府的硬性約束相對較少的民營企業內部,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的員工對傳統性的認可程度比較低,所以能力和貢獻成為了員工進行歸類的重要特征,而報酬契約的差異就是能力和貢獻差異的主要外在表現。員工會傾向于服從因能力和貢獻產生的報酬契約差異的權威性,并且民營企業不像國企那樣有維持社會公平的義務。此時如果再保持報酬契約的同步性,則同樣會產生一種結構性摩擦,這種摩擦會造成對經理人的激勵不足,從而影響企業效率。因此為了減少結構性摩擦產生的進一步交易成本,對于經理人的嵌入性結構選擇也就更傾向于影響力對稱的關系結構,對于經理人的選擇更多的是依靠市場選擇,而對于經理人的報酬契約管理也更多的講究在關系合同軟化的前提下向市場治理靠攏,由市場的供求決定,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能夠更多的在民營企業發現多樣的報酬方式,而在國有企業則相對要簡單的多。
四、結論
對具有嵌入性結構特征的企業報酬契約的分析表明,對于具有高度資產專用性的經理人投入的人力資本而言,完全通過市場治理顯然是不符合它的交易特征的。而為了維持企業經營的長期穩定,引導經理人的利益目標盡量向股東的利益目標方向發展,股東只能通過合同約束出現軟化的關系合同來治理經理人的行為,通過企業內部部分產權的模糊與轉讓來達到對經理人的長期激勵。而對于不同產權結構的企業而言,在為了最小化已經增加的交易成本下,對于關系合同治理的嵌入性結構的選擇應該要選擇與企業產權適應的同構結構,以防止結構性摩擦,從而使股東與經理人建立的關系產權更加好的發揮作用。
核心關注:拓步ERP系統平臺是覆蓋了眾多的業務領域、行業應用,蘊涵了豐富的ERP管理思想,集成了ERP軟件業務管理理念,功能涉及供應鏈、成本、制造、CRM、HR等眾多業務領域的管理,全面涵蓋了企業關注ERP管理系統的核心領域,是眾多中小企業信息化建設首選的ERP管理軟件信賴品牌。
轉載請注明出處:拓步ERP資訊網http://m.hanmeixuan.com/
本文標題:企業經理人報酬契約的嵌入性結構分析